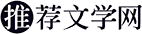就这样,过了30岁的某一天,达从澳洲回来探亲,那是暌违了7年后,我再一次见到他。达先看望了耄耋之年的外婆和外公,随后来到了我家。坐在客厅里的他,有一种放浪形骸的颓废,和厌倦一切的玩世不恭,他身上所裹挟的长途旅行中和遥远世界里的尘埃在我整洁到一丝不乱的家里慢慢扩散,仿佛一台过热的引擎始终驱驰着他无法停歇,我似乎听见他那长久奔波的灵魂在故乡的清凉空气里暂时冷却下来的嘶嘶声。尽管如此,令我欣慰的是,还是同当年一样,他用没有任何伪装的眼睛真挚地看着我。父母准备着各种零食和话题,我则陪坐在一旁,作为童年的玩伴和故乡的主人,我必须得说些什么。
除了寒暄和慰问,我俩共同的话题依旧聚焦在电影上。我取出小小的盒子,告诉他这个移动硬盘里存放着包括成人电影在内的许多影片,这些影片的总长度其实就是我俩分离时间的总和,其内容之丰富情节之离奇也许并不逊色于这些年来他的在外的经历和见闻。我没有避开这些电影附着的“死亡”和“性”的元素,记得一位作家说过,人总是要死的,也十有八九要和女孩困觉的,因此,避而不谈反倒是一种虚伪和矫情。这些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很强的艺术性、哲理性以及充满异国风情的影片,每一部我看后都写了影评发表在博客上。我如此一说,达接过盒子,抚摸着这月光宝盒似的阿拉丁神灯似的手掌般大小的东西,淡淡地笑了笑。
在他停留于故乡的2个月的时光里,这个盒子一直伴随着他,正如一直伴随着我一样。数年后重逢的我们都过于矜持了,因为在各自孤独的道路上已走得足够遥远了。我们已经相互远离到了仅仅看清彼此小小身影的地步,而再也看不清各自的面孔。缺失了当初那因毫无阅历而极易被感动,进而剖肝沥胆的激情和纯真,我们早已经学会在这世界生存的技巧,彼此戒备和防范,轻易不让任何陌生的东西侵入自己固守的地盘。所谓成熟,就是这样一种令人悲哀的东西。
在他“去往”或者叫“返回”澳洲之前,我俩去了新建成的高达300多米的市中心商业综合体内看了最新的电影。这地方曾是我和母亲一同看第二遍《泰坦尼克号》的新华影院的旧址所在。这是一部好莱坞的动画片,虚幻做作而又十分逼真的3D动画电影,似乎将真实世界动漫化的同时,又保持着治愈现实的某种天真和竭力搞笑的庸俗色彩。观众被电影里的许多“包袱”逗乐,被从现实窘境中提炼而成的尴尬和自嘲呛出一连串笑声,就像被胡椒粉呛出一连串喷嚏似的。因为不是原版英文对白,早已适应西方电影的达开始时还不满地叹息了几声,不过在影片结束之时,他还是满意地咂了咂嘴,由于高度兴奋而满面红光。随后,吃了一顿西式快餐的我们就在高耸入云的城市地标前的车站匆匆分了手。公交车从远处缓缓驶来,不知何时再相见的落寞感蓦然俘获了我。虽然不至于再次陷入当年失去好友失去梦想的恐慌不安中,但我依依不舍的目光还是追随着上了公交车的挚友的身影。明亮的夏日夕晖照进车中,令车内的金属和塑料反射着光线而熠熠生辉,车内的一切像个透明盒子那样纤毫毕现。巨大的车窗玻璃仿佛一扇神奇的橱窗,划出了我俩世界的分界。那光洁的玻璃既反射出车外我的世界,也透现出车内达的世界。我看见即将返回那冬季的澳洲,有些秃顶驼背的挚友蜷缩在窗后座位上,马上低头漠视了故乡的风景,掏出了手机。此后,无声的离别中,直到公交车滑入熙攘的人流和车流中,淹没在市井的喧哗里,消失在我的视野外和故乡的世界尽头,他都再没有抬起头来。
我感到眼中溢出了湿湿的东西,抬头望天,一颗雨滴也没有的夏日晴朗正统治着一切。
《黑客帝国》构建了一个想象中的但绝非不可能的未来世界。这个世界中,没有太阳也没有生机,没有爱也没有自由。冰冷的高度理性的机器统治了世界,并将可怜的人类作为“庄稼”来种植,成为其巨大能量的唯一来源。为了让“他们”成为“它们”,毫无抵抗且毫不知晓地用奴隶的一生来成为机器所需的一节节电池,机器让程序设计师编写了囚禁人类思想的程序,编造了令人类永远安睡永远迷失的梦。而这个梦,就是被称为“现实世界”的东西。
现实如梦,色即是空。
在第三部影片的结尾,一场人机大战后,不想苟活在虚幻梦境中的逃脱机器控制的人类抵抗者得以幸存。设计师问唤醒人类的先知,人类同机器达成的和平将持续多久?先知意味深长地回答:
“持续到不能持续为止。”
任何的和平都是脆弱的,任何的真相也都是残酷的。用巨大的代价所换得的东西,也正是其珍贵价值之所在。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历经挫折的我越来越觉得内心的平静和真实是极其珍贵的。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认识并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再设置那些高不可攀的目标,找到并安适于这个世界中独一无二的位置,觉察到自己的极限和阈值,并好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认真从容地生活着,这是多么伟大又多么平凡的领悟!在越来越多的人离我而去的时候,我其实并未感到多么遗憾和恐慌。相反,寂寞令我能够沉入自己的内心深处不断发掘,让那些沉睡在心底的纯真美好的情愫,如古城中的老井般重见天日。坚定地回溯那温凉沁人的井水之源,也许某天,就能够在更深的地方,发现那隐秘而巨大的地下水脉,从而与这个世界中的许多人的心灵水脉重新连通。
没有人逼迫我嬗变,也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令我去削足适履,保持内心的鲜活和灵魂的自由,从而让生活变得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生存的智慧不在书籍或课堂中,也不在人云亦云中,而在个人的体验中。能够遗世独立的资本,正是我不变的坚守,和用这不变来应对瞬息万变世界的能力,这是随着年龄增长我越发熟练掌握的生存技巧。在新千年之后的漫长时光中,我看似一事无成,无论是升学,就业还是婚姻,是这些标准人生进程的局外人,在这个程序化的世界中格格不入,特立独行。而如此这般的我并未为之气馁、慌乱或感到挫败,反倒于水穷之处坐看云起,于峰回路转处邂逅柳暗花明。独善其身的我明白自己是在这个浮世中逍遥,像风中的花粉,如水中的浮萍,于飘游沉浮中积蓄着生命宝贵的能量,寻觅着栖身的美丽绿洲,寻觅着那化为璀璨的燃烧迸射的那一刻。我不诅咒无情的逝川,不惋惜那萧萧的落木和滚滚的江涛,而是坦然接受岁月的变迁,并从未放弃过梦想和努力。一次次攀上那座位于城市南郊屹立万年的隐者之山,我感受着千年前古人高贵从容的寂寞和闲适清雅的诗意。屹立山巅,须要悠然如浮云的姿态,以及平静如深潭的心灵。而在喧嚣浮躁的山下世界中,人们其实并未在忙碌的追逐和焦虑的竞争中感到由衷的满足和真正的自由。
2000年,我18岁,若干年后,我跨过了20岁,若干年后,又跨过了30岁,如今,正向着40岁的大门行进着。数百部电影和数百册书,充盈着我平淡清寂的生活,化作内心的丰裕与灵魂的清奇。我写下了上百万的文字,有诗歌、散文、小说、影评和书评,还有盒子电影院,依旧在那。这些大大小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彼此替代的盒子,见证着我的少年,青年和中年的岁月。我发现了镜中的白发,头顶也变得日益稀薄,不管我愿不愿意,伴随着成长,衰老也必然无情到来。如同季节自然交替似的,从少年的春季走来,渐渐走到了青年的夏季的尾声,秋天正带着萧瑟的凉意和远方的肃杀向我逼近。记得在电影《失乐园》中有这样两句对白:
“看来,漫长而寒冷的季节就要到来了呢!”
“没关系,夏天的热量足以令我熬过凛冬。”
夏天的热量,永远的盛夏!那时,我和达漂浮在只在暑假开放的露天泳池中,谈论着电影,游戏以及各种令我们痴迷和兴奋的东西。那波光粼粼的池水中,太阳的倒影仿佛悬浮于蛋清色泳池里的一枚可爱的蛋黄,沉浮于温暖羊水中的一个沉睡的赤子。泳池四周是陈旧的楼房所围成的仿佛井壁般的世界,这个世界无比安逸也无比脆弱,水的浮力轻柔地托举包裹着我们,宛若母体的子宫。我们其实并未真正学会游泳,也没有在除了泳池之外的任何一片开阔的自然水域中搏击过风浪。我们只是在兴致所至的时候,在泳池的50米泳道上勉强游上一个来回,便气喘吁吁地漂浮着,在散发着漂白粉味和塑料味的水面上聊天,露出雪白丰腴的肚皮在阳光下假寐。记得有一次,即将去往澳洲的达是这样在泳池里谈到未来的,他说:
“我们还没干过什么事业,我们干过的,充其量,不过是训练而已。”
我闭上眼睛,脑海中便浮现出那个灿烂平静的泳池。诚然,我们在无休止地训练,就像永远不会投入战争的军队那样不断地操演,徒劳地磨砺着尚未沾上血污的刀枪,在迷茫中等待,在等待中迷茫,在时间中彷徨,在彷徨中重复,尝试和希冀。无论是学习,工作,恋爱,抑或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成长和蜕变,其实都只是一种浅薄的小打小闹和装模做样而已。冰冷、辽阔、深邃,孕育着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也展现着无限沧桑与残酷壮美的大海还离我们相当遥远,那无比浑浊摧毁一切的滔天巨浪甚至永远不会出现在我们的人生之中!啊!我们所见识到的,只是存在于地表的、浅浅的、清澈的、缓缓流淌着的、企盼着终有一刻汇入那遥远而浑浊大洋的一道涓涓细流而已。但,百川归海!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的目标是大海,我们的梦想是大海,我们的终点一定是那片大海!
那片大海,既是生之源头,也是死之归宿,那里泯灭了悲欢,消弭了生死,吞噬了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也释放了所有的激情和自由。它是世界的尽头,是永恒的存在。
生命的最初,我发现了,外婆家的天井上方,是漂浮着星辰的宛如一片大海般辽阔深邃的普鲁士蓝的夜空;我也曾邂逅,那座石砌的祖父的农村老屋前,有一条不舍昼夜流动着的被朝日和夕阳照得金黄发亮的动人小河;我更铭记着,在长江附近的小街上,从自家公寓的阳台上醒来的时候,看见盛夏的旭日正从远处工厂的烟囱后方冉冉升起,在西邻的金属窗框上映出那铁水般炽热而浓烈的橘色霞光!那时候,这个世界同我的幼小的心灵一样,是平展的,辽阔的,轻盈的,毫无皱褶的。这完美的无垠的世界,就是被称之为童年的世界,被称之为故乡的世界,被称之为梦想的世界!
曾几何时,我悄悄拥有了这个璀璨旖旎永不消逝永不失落的梦想,这深藏于心底的童年和故乡。我将生命初期邂逅的人和故事寄寓在如今现实的某处,这个世界的某处,伴随着渐渐长大,也将它珍藏于那些小小的盒子中。它就像一个隐身在盒子里的小小的精灵似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只有我自己看到,只有我自己能够将它唤出,与之共鸣、共舞、共醉!于是,这个被称为电影的精灵,便成为那童年梦想的载体和化身。它隐含着梦之世界的影子,蕴藏着解读整个宇宙的密码,它是我人生的寓言和缩影,是一面能映照出心灵奇妙风景的魔镜。通过它,我能够听到各种故事,品到各种人生,收获各种感慨和领悟,并依然能在它的光影变幻中找回当初那个最完美最真实的自己,依旧能触摸到那个最初始最绚烂的梦想。我能够进入其中,久久不愿出来,也久久不想被发现,像是和这个残酷而纷乱的现实世界捉迷藏似的。童年时,我曾读到一则童话:厌倦一切的男孩走进了一幅画中,他的书包还挂在画中的一棵树上,人却踪影全无。寻找男孩的父母和老师只能在画外的世界中徒劳地呼唤和寻觅,而不知近在身旁的画中却另藏乾坤!男孩与他所消失的世界,及其所经历的一切,无人察觉,无人知晓。
无人知晓,这个词透出一股孤寂和凄凉,同时也隐含着一种自由与神秘。进入画中的男孩并非遭人遗弃,也并非自我放逐,相反,被贴上“顽劣”而“孤独”标签的他其实是在追求一种人生的纯粹和极致。那是一种永不放弃与徒劳无功的奇妙混合,是一种不断失去又不断寻觅的人生姿态,是一种不断失败又不断重来的执拗坚守,也许,这才是梦想的本质和真正的滋味!在澳洲的海边,据说已重新拿起童年的炭笔和画板的达,他的身影并不被故乡的人们所知晓。因为,他消弭在无数相似的渴望接触到现实中大海和描绘梦想中大海的生命海洋中,这些生命听着如雷贯耳的海潮,看着万马奔腾的海浪,以及视野极限处,那亘古不变的水天一色的湛蓝的海平线。哦!他们在自然的静谧中体验着生命的躁动,将自我的那一道鲜艳独特的色彩融进那黑白无常的浩渺宇宙中,让人生的短暂被吸进存在的永恒中。这奉献了自身才获得的博大与永恒,自由和极乐,是上帝对追梦者的最宝贵的赏赐!
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他身处于怎样的世界,无人察觉;这些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无人知晓。他隐藏了曾经的自己,甚至埋葬了曾经的自己,幸存下来的,也许只有伤痕累累且早已嬗变的孤独灵魂。别人不再问起,他也不再谈及,甚至不再触碰那个已经失去色彩和温度的梦想残骸,但这并非由此证明他已然失去了梦想,抛弃了梦想。梦想依旧,不过不再如当初那般轻盈可掬,而变得如今这般沉重难负。
但至少他实现了离开泳池去追逐大海的梦想,而我却依旧漂浮沉睡在故乡的童年的泳池中。要说我俩的区别,没有比这更大的分野。
《黑客帝国》自公映以来,“现实如梦”的理念,从此被许多电影所模仿、复制,也被许多观众所痴迷、津津乐道。这些或是科幻,或是悬疑,或是哲理,或是动作元素的后来之作中,无一不是将人类的梦境渲染得陌生且奇特,反转、解构或颠覆着现实,治愈、拯救或重塑着人心。仿佛这奇妙梦境便是尚未被证实却有着无限可能的平行宇宙似的。也许,在我们的内心中,的确存在一个游离于现实的陌生而奇妙的平行宇宙。在其中,所有缥缈如烟的梦想、所有羞于出口的憧憬都得以实现,那里是所有人的所有梦想尚未折戟沉沙的黄金时代!那里有雄伟壮观的楼兰古城!那里有刚刚建成的直刺苍穹的埃及金字塔和耗尽心血也充满血腥的罗马竞技场!那里的青铜器不是黯淡无光的青绿色,而是灿烂夺目的金黄色!散发着灼热逼人的金属与火焰交媾的气息!而现实中,千年后的它们虽破旧而残缺,但这些断瓦残垣,这些遗址和废墟,这些布满铜锈的伟大的重器和雕塑,谁说不是依旧能构建平行宇宙的材料?!谁说不是依旧能唤醒与迸发想象的母体?!谁说不是依旧能守护梦想的神秘家园?!坚守着和流浪着的我们就是这样孕育着这个宇宙,怀抱着这个宇宙,流连在这个宇宙中的!我们一边悄悄地构建着这个无比绚烂无比温暖的内心宇宙,一边继续囿留在黯淡苍凉的现实世界中,或者说,只有如此方能够存活于现实世界中。
另一些时候,这内心宇宙并非全然与现实世界对立或隔绝,而是忽然透出些许闪光,显露出些许令人狂喜的凤毛麟角来。比如我的影评忽然大受好评,阅者过千,赞者过百;而达的一幅画作终成为一件引人注目的艺术品。这样的高光心醉的时刻虽然不多,但足以带来继续前行的热能和动力。
在另一部发人深省的电影《路》上,在末日世界中踽踽独行的濒临死亡的父子之间,有着如此的对白:
“你不能将自己的精力消耗在过去没有发生,未来也不会发生的事物上,现在,你必须集中精力。”
“好吧。父亲。”
这样的事物,就是白日梦,脱离实际的幻想,逃避现实的蜃景,会令人失去在现实中求生的力量。尽管在现实中,我们也许活得像一只秋后的蚂蚱,短暂而虚无,羸弱而苟且,但即便是蚂蚱,也有活下去的欲望和资格,也有将一日当作十年的珍贵生命,也会在严苛无情的现实中奋力求生,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
在这篇宛若20余年来的自叙传的小说的结尾,我还是想起了15岁那一年的那个晚上,那个改变我一生的暮春之夜。那一夜,我和马虎在茫茫大江边的小小公寓中,在父母的卧室里看的那部电影。当巨大的战争机器缓缓碾过黯淡失落世界上积存的累累白骨时,那轰鸣作响的马达声和咯吱咯吱的碾压声悄然渗进入了我的灵魂,那刺眼的激光束伴随着空中飞舞子弹的嗖嗖声震撼摇曳着我的心灵,需要战斗搏杀至死方休的未来拉开了它神秘的巨大帷幕。秘境般新奇美妙的光影和声响照亮和响彻在我那15岁的平凡世界中,仿佛是天启,仿佛是洗礼。从此之后,那枚天外来客般的火种,如从宇宙深处飞来的流星般划过茫茫暗夜,坠落在我的世界中,引燃了一切,火光冲天。当我内心中那片不谙世事的杂芜的野草被烧尽后,那袒露出的丰饶而赤诚的大地上,开始出现了生机和萌芽。作为生命之源的梦想火炬从此一刻不停地明亮剧烈地燃烧起来。从那时起,我的内心就像是打开了一个神秘的盒子,而我的命运就开始于那个盒子。盒子里的风景一下子就占据了我人生舞台的中心位置,梦想的火炬将这舞台上的风景照得纤毫毕现。这浓墨重彩、无比动人的风景宛若千年的壁画和神祗的殿堂那样神圣庄严。随着这个打开的盒子而来的,是其后漫长岁月中不断经历的各种酸甜苦辣的人生体验。正如潘多拉的盒子似的,从里面也飞出了许多不祥的苦味和难受的涩味。而盒子的底部,却还留存有被称之为希望的珍馐。小心翼翼地护佑着这道珍馐的我,即便在沙漠中跋涉,在荆棘中穿行,那发现绿洲抵达天堂的梦想一刻也未从脑海中离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尾处,修士阿辽沙这样对纯真正直、骄傲自负,爱憎分明且渴望改变世界的男孩柯里亚说道:
“你将会成为一个终生不幸的人,但这样的人生依然会得到祝福。”
我愿做一个忠诚于内心的人,一个将梦想和自由视若生命全部的人。即便梦想遥遥无期,即便不幸如影随形,但我知道,我是被不断祝福着的。这是一道幽灵绝美的魅影、也是一束上帝温煦的目光般的祝福,令奋斗至此的我无比幸福,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