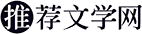对我来说,一九八八年算不上一个好年头。
那年的秋天刚刚来临,金黄的稻谷已经像一座小山占据了我家的半间屋子,我父亲脸上的沟壑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而我十几岁的脸庞上,却深深地刻着几道高考落榜的愁容。
一个很有诗意但在我看来却有些颓废的黄昏,坐在已不再汹涌的澄江南岸,看着那轮光芒黯淡的圆日渐渐地沉没于西山,我的心在不停地想,我没有理由要在这岸上辛劳一辈子,即使去做流氓,我也不会像我父亲或我家那头老牛一样,围绕着三五亩瘦田,不知疲倦地挥霍青春岁月。
在我的身旁,还坐着与我一起落榜的蔡马师,我看了看蔡马师那有些模糊的面孔,那面孔里似乎正弥漫着许多奇异的幻想。这时我发现,我和蔡马师就像两只刚刚长齐羽毛的公鸡,都没有飞越一九八八年的大学和中专录取线,只好一同垂头丧气地回到这澄江边静坐、徘徊和忧愁。
我的父亲没有用做父亲的慈样和挚爱来抚慰我有些伤寒的心灵,他倒是在幸灾乐祸地氤氲中,一心一意为我张罗他梦寐以求的婚事。父亲理想中的儿媳是北村的翠竹,我和翠竹在我们十二岁的夏天里,成为我父亲和翠竹父亲张久贤一拍即合的牺牲品。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已是一个女人的未婚夫,我一直背着这只“未婚夫”书包,念完了小学的五年级、初中和高中。我不喜欢这门亲事,但这不是说我不喜欢翠竹。翠竹像 一棵绿色竹子, 在我的心目中随风晃动。那修长的影子时常搅得我无法安宁。
在我的故乡花香村,我父亲的眼光算得上是一流的,但它却没能越过延绵的青山,抵达城里那些姣甜的面容中,感知到乡村永远也无法企及的鲜艳和妩媚。父亲还不知道,他儿子心中的那片土地,已种满了对城市的崇拜和向往。
木立在老历八月的水田里,我看见初秋的太阳已来到我的头顶。整个初秋的画面,显得炎热又宁静。父亲像一架机器人,准确无误地插着晚稻秧。
我说,爹,我得去补习。这句话像一碗旧饭,已被炒得有些变味了,我希望父亲能在这明丽的阳光下为我松口。“把婚事办了,做什么都由你。”父亲直起腰来,望了一眼睛朗的天空。
我只好保持沉默。在沉默中,我看见父亲的动作依然麻利,步伐依然稳健。我想父亲就像一块顽固的石头,容不下半点可以种植商量的土地。浑浊的田水在我的小腿间悠悠晃荡,细嫩的禾苗在田水上浮动并舒展着有些疲惫的笑容。我的身后,还有一片茫茫的田水,那田水似乎已洒散成海洋,逐渐将我和父亲吞没。
一丝恐惧和绝望瞬间击痛了我,令我头晕目眩。我把手中的秧苗狠狠地摔在田间,气急败坏地冲着父亲说,我不干了!
我从我姐们的 家门口走进又走出。我的大姐二姐三姐和四姐,都已分别嫁给附近的四个男人。但她们没有谁敢在父亲的眼皮下给我去补习的学费。我想不是她们不敢给,最主要的还是她们都不愿意我去补习。她们共同愿意的是我立即娶了翠竹。从我姐姐们的眼睛里,我看见翠竹带给她们的嫉妒和爱惜。
是啊,翠竹可以令很多女人黯然失色。可翠竹已经十九岁了,我想十九岁的女人,大概都不尽情愿拿自己的青春去孤独或拿去作不知结果的等候。而我最需要的还是学费和读书。翠竹的青春和她身上芬芳的气息还不是我迫切需要的东西。
在不停地奔走之中,开学的日子就滑过去了, 而我和父亲仍像一少一老的牛,对峙着互不相让。
补习的希望,像黄昏的太阳,已被起伏的群山吞噬了,在没有希望和憧憬的日子里,我与蔡马师成了形影不离的兄弟。在从我故乡花香村通往东江镇的路上,蔡马师说,读个鸟书。我读了三年高中,越读越朦胧。我说你这狗日的,能补习不去。老子就是没你这福份。这样说着,我们就同时落入东江镇街上拥挤的人流中了。
赶圩的人们,脸上都挂着丰收的喜悦,买卖的声音像飞扬的尘土,弥漫着东江镇的天空。蔡马师把预备好的编织袋塞进我手里,我便小心翼翼地跟在他后面,挤到臊味熏天的猪肉摊。
蔡马师伸手在一绺一绺猪肉间,装着一本正经地挑选,趁屠夫为别人称肉时,就快捷地溜一块进入我等候在案板下的口袋。蔡马师做得很熟练,而我却胆颤心惊,总害怕屠夫那把锋利的杀猪刀刺向我的心口。但我又不想放弃这种冒险。在我们停止作业时,已经有五绺肉入袋了。
提着一袋子的惊慌和喜悦走入粉店,我们换到了十四块七毛钱。我嘘了一口长长的气,不管如何,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用“劳动”换回的钱。
我和蔡马师买了两张去县城的火车票,在火车上,我说老蔡,这种事以后不要叫我了。蔡马师滑出一串没有声音的笑容说,干坏事就像恋爱一样,需要不同的花样,你恋过爱吗?
蔡马师这一问,问出了我一身的冷汗:我没想到蔡马师的坏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蔡马师对我的惊疑不屑一顾, 他说你永远也想象不到,我在县城读书的这三年与我的哥们干了多少有意义的事。而你就只顾念书,但结果却是一样,你看我们, 就像一条藤上的瓜,一条藤上的两只苦瓜。
火车到达县城并把我们扔下后,又嘶鸣着前进了。我和蔡马师在昏暗的路灯下朝我们读了三年书的学校走去。
望着静静的校园,我的眼泪竟忍不住地往外流了。今天是星期几呢,总不会是星期天,不然校园就没这么安安静静。
我们走过了篮球场,随后又转入足球场。足球场上的草已在不断地干枯了,踩在上面,再也体会不到青草滑溜溜的弹性。但我还是躺下来,尽力地伸开四肢,面对着被静谧幂罩着的夜空和夜空里的星星,回忆着如风而逝的三年里所发生的一切细节。
蔡马师也躺在草坪上一声不响,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第二天的中午,我说老蔡,我们还是回家吧。这个时候,我想也只有村庄才是我们最留恋也最需要的地方,校园和城市的大街,都是别人的。
蔡马师冷冷地回答我说,没钱了,我们先得找点路费。我只好跟着蔡马师毫无目的地在汽车站的附近转悠,蔡马师猛然转头截住一个斯斯文文的小伙子说,老三,你还认得我吗?那人朝着蔡马师左看右看后,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蔡马师像是有些焦急地样子,赶忙说,哎呀,你怎么忘了,那时在老大那里,你不是托我要样东西吗?
我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看见那人像是被淋了一头雾水,他说哪个老大,我也没托你要什么呀。
蔡马师凑上前小声说,你想要的枪,我已搞定了。怎样,今晚到老大那里要去。
我有点惊讶,心里莫名其妙地想你蔡马师什么时候搞到枪的。那人只是说你认错人了,并迈开步子。蔡马师跟上去说,我没认错,你太不够兄弟了,怎样,兄弟没钱吃饭了,请个快餐吧。
那人随手掏了十元钱给蔡马师,有些惊慌地转身大步走入人群中。我凑上前说,老蔡,你真认得他?
蔡马师狡黠地一笑, 说认得个屁,这全是以前跟哥们使用的,不然,我们得走路回家了。
东江镇的火车站冷冷清清,我和蔡马师下了车就直接奔上了回村的路。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我完全被围困在蔡马师那些对往事滔滔不绝的叙述里,那些叙述像是房顶上的炊烟,一阵风轻轻地吹过,痕迹就完全消逝了。但蔡马师依然乐此不疲,把他的那些绝活统统炫示于我的耳畔。
我说,老蔡,你口渴吗?
蔡马师没有体会到我的意思,说还真渴呢。这时我们恰好路过一片甘蔗林。那些等待着被镰刀戕杀的甘蔗,正斗志昂扬地挺立在阳光之下,毫无生命受到死亡威胁的畏惧。蔡马师快捷地跳入甘蔗地,只“嚓、嚓”两声,便折了两根甘蔗跑出来。还没等他喘上 口气, 就听见远处有人在喊:快把甘蔗放下。循声望去,只见有人朝我们这边跑。
蔡马师说,只好跟他赛跑了。令人痛心的是,我和蔡马师都不是跑步能手,只过两个山头,我们便在这场痛苦的比赛中败下阵来。
“哪个村子的?”“花香村。”
“为什么乱偷甘蔗!”
“口渴。”
“你以为是你家的吗?”
“不是。”
“走,找你们村长去。”
我和蔡马师像两个俘虏,被人赶进自己的村庄。但事情很轻松地解决了。那人没想到他很快就找见了花香村的村支书,但他更没想到花香村的村支书陈书山是我的父亲。一阵交涉之后,那人便扛着两根长满叶子的甘蔗循着来路回去了。
老历十月的月底,河水有些寒意了,我去补习的希望已完全地结成了清融的冰块。父亲强行要为我举办婚事,毫不考虑我的态度。
父亲说,你陈有路的青春没人可怜,但人家翠竹的青春可耽搁不得呀,而且,不找个女人来压压你,我看你非得成了烂仔不可。
我的四个姐姐也乐呵呵地来助父亲的兴,忙里忙外地帮我收拾房间。随后几天,在别人的欢乐声中,被打扮得花花绿绿的翠竹打着花伞骑着马,走出北村,踏过澄江桥,再进入南村,来到我的面前,成为我的新娘了。
我像是做着一场青天白日梦,还没对人家说过一句贴心的话,就成为人家的丈夫了。我相信,这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更简单的婚姻了。夜色一来,我就偷偷福到北村的蔡马师家了。在蔡马师父母的审问声中,我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想当农民。
父亲对我的这种潜逃也无可奈啊,只是不知翠竹她怎么样。我感觉有些对不起她。我希望翠竹不要怪我,怪只能怪我们的父亲。
三天后,翠竹回娘家去了。按风俗。在一年内,只有在节日,她才能回所谓的婆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说。我可以在自己的床上过夜了。夜里。嗅着有女人体香的空气,有些无所适从。我想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不是一种病呢?我猛然被这种疑问给吓了一跳。随后就难于入眠。
距我人生第一次失眠之夜的两天后,我和蔡马师相约从东江搭火车到了贵州省一个叫龙风的县城。我曾跟随父亲多次来过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有一位我叫她做三奶奶的老人。
当我带领蔡马师踏入我三奶奶的家门时。我看见坐在堂星里的三奶奶神态安详、面目慈善,于是我感觉像是真正踏进自己温暖的家屋。我那官至旧军旅长的祖父共娶了六个老婆。祖父在1949年战殁后,我的祖母们便一个接一个地撤手人寰。三奶奶是唯一健在的。
三奶奶看见我时,也流露出惊疑和喜悦的表情。三奶奶说,你不是刚完婚吗?我说,家里现在空闲,我们过来找点工做。
三奶奶让我们帮助开录相厅的叔叔守门和卖票。我们干得相当的卖力,尽管录相室里的打斗声令我们热血沸腾,我们还是能不慌不忙地始终坚守着阵地。
但过不了几天,我们便不再那么一本正经了。在蔡马师的唆使下,看见有漂亮的女人独自要买票时,只要蔡马师给我使个眼色,我便说,只要让我们摸一摸可爱的小手,就可以免费入场。我们的这种做法吓跑一些姑娘,但另一些姑娘却很干脆地伸出手让我们抚摸,之后便摇摆着入场。
我们在无偿的享受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快慰。最终,叔叔发现了我们的把戏。理所当然,三奶奶把我们逐出了她的家门。举目无亲的我们,又只好走上了回家的道路。
我父亲为我谋了一个职位:东江镇花香村青年干部。父亲说,还有二十天,全县就要举行招干考试了,你复习复习,说不定还能考中。
在我捧着一些有关招于考试的书籍时,天气的凉意就越来越浓了。
又是一个黄昏,我独自漫步到澄江的南岸,看着两岸被秋风摆摇的绿竹,我便产生了一种对翠竹的深深的懊悔。踏上澄江桥,我看见澄江水已瘦了很多,而这澄江桥也有些破旧,我不知道,这桥还能经受多少次洪水的考验。
这样想着时,翠竹已从南岸踏上桥来了,我不知所措地等候她的临近。翠竹低着头,红着脸从我身旁走过,我像是一座雕像,看着也走过身旁、出桥、踏过南村的土地,最后消逝。我发觉,这是一个看似平淡的场合,但是在这种场合里,能装出无动于衷,得需要很大的智慧和勇气。
是啊,什么语言能比得上沉默呀。情不自禁,我发出了一阵声音平缓的笑容。我感觉到这笑容有些凄凉和沧桑,不像是十九岁,而应是九十岁。谁也不会相信,一对无仇的夫妇在桥上相遇,竟然连招呼都不打。
回到家时,夜色已覆盖了整个村庄,我看见我的家里来了一位不寻常的客人。
父亲说,这是县上的宋主任。这夜,我把床留给了宋主任,我则在 堂屋里读书到深夜,再从深夜读到天亮。
清晨,宋主任离开我家时,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会有出息的。宋主任像一位伟大的预言家,因为我终于循着他的预言走进了招干考试的试场,并考出了全县第一名。
一九八九年的春节过后,我终于走进了县府大门,成为一名秘书。我是国家干部了,那一刻,我露出隐藏了十几年的最为真实和灿烂的笑容。我父亲也甜蜜地笑了,他似乎完成了望子成龙的壮举。
笑完之后,我开始憎恨我的父亲。我想父亲一直像一座山,压得我身不由己,尤其是那场婚事,将使我的青春和以后的岁月失去绚丽和浪漫。
我在拼命地学习业务知识和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草拟了一份上诉书。我把父亲陈书山和翠竹的父亲张久贤的名字一同诉之于法院。这就是说,我要告我的父亲和岳父包办婚姻,并请求通过法律来解除这一切。
三月的桃花压满了桃树的枝条,一簇一簇的火红点辍着春天,使我的心情感到无比的舒畅。
东江镇的法庭上。被告之一,我的父亲陈书山缺席,翠竹的父亲张久贤面无血色地站在被告席上。
我请的代理人是蔡马师。我想有理不用声高。我只是和蔡马师各自买了一套相同的西装,并把头发梳得油光可鉴。开庭这日恰好逢着东江镇的圩日,于是,法庭内外挤满了人头。我想,每个人都在怀着好奇的心情来观看儿子告老子的案件,并等待一种有滋有味的结果。
法官问:“原告,你和翠竹已发生过夫妻关系吗?”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蔡马师已抢着说:“我作证,他没有。”随后,传来了一阵猛烈的笑声。我的脸一下热得像渗破了皮。
法官说:“请原告讲。”
我回答说:“没有,连一指头都没碰过,不信你去问翠竹。”又是一阵浪潮般的嘘笑声。法律终究是站在我亲这边,按法官的意思在说,这是一场真正的包办的婚姻。男女双方年龄都未达到法定的婚龄,法律当然裁决原告胜诉,婚姻不得不解散。
父亲在得到结果之后,迅速通知我回一趟家,说是有要事相商。
看见父亲时,父亲的脸色有点使我不寒而栗。是啊,我发现自己做得有些过火了。但这一切就 像一缕云烟,已被一阵风轻轻地吹过去了,什么也无法挽回。
父亲拿出了多年已未使用的算盘。父亲说,这是一把跟随我多年的算盘,我很久没跟人算帐了,今天,我不得不跟自己的儿子算上一次狠狠的帐。
父亲说完使用抹布抹了抹灰尘,并活动着指关节拨打着珠算子。珠算子发出的清脆的声音一时感动了我,我记得多年前父亲使用过这把算盘。当时任生产队会计的父亲,其手指间滑动出的富有节奏的声音,在我幼小的心灵间留下过许多痕迹,并在我此时的心里索绕回荡。
父亲说,你七岁入学前的帐不用算,那算我白养了你,但七岁之后的帐不得不算。说完话后的父亲仍是一副铁面无私的表情。
父亲拨打珠算子和嘴中念念有词的声音, 弥漫着整个屋子。一家人无声息地听着声音的扩散,个个面色凝固得很庄重,这似乎有点像在共同倾听着一曲哀乐。
父亲说,一共是三万八千块。
我点头默认。但我的母亲和四个姐姐都放声哭了,哭声很齐整,像是事先已有预约。父亲说,我们要断绝父子关系,待还完帐后你才能离开这座屋子。
我说,写张欠条可以吧。
父亲说,可以。我便写了一张欠条,之后,我用小刀戳破了手指,一滴热血瞬间蹦出来,溅在欠条上,我再用拇指蘸了鲜血摁住我的名字。我看见我的名字“陈有路”鲜血淋淋。
我独自走出了我故乡花香村,身上背负着的是三万八千元的债——一十几年的养育之思。我被因“考核期间道德修养差”的理由拒绝在干部的大门之外。
一九九八年的秋天里,我站在深圳市平湖工业区一个叫远安厂的的草坪上,把一封电报读得相流满面,电报是蔡马师发来的。上面是有关我父亲死亡的讯息。
近十年了,我没见过父亲的面,也没有见过任何亲人。
三万八千元,我已还清了。而听说,翠竹还没有嫁人。
我在被拒绝于干部的大门之外后,我时刻都滋生着想回家看看的心愿,我怀念那里的山,怀念那条碧绿而且温驯的澄江河。但我没有回去,我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不要想念那方土地,而在每一次的强迫之中,我却发现自己的双手在发抖,双腿在打象,心在收缩,值得自豪的是我始终没有流泪,尽管我经历了流浪、做苦工、生病和挨饿的岁月。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我来到了深圳,卷入结浩荡荡的打工大潮,并用自己心力默默地工作。我一直在认为,一个男人不必为他过去的行为伤怀和苦恼,他应该勇于承担今天的担子。但我又时常冲毁自己的这种“认为",独自一人为过去懊侮,我懊悔自己成不了父亲眼中的好孩子,也懊悔翠竹的青春被我狠狠的戳了一刀。我等待漂泊岁月尽快结束。我已厌倦了流浪和打工的生活,也不再有当干部的念头。我想,有可能的话:我会真诚地去娶翠竹,并一丝不苟做农民。
“我认输了,爹。”跪在深圳的一块草皮上,我喊出冷漠了十年的那个称呼。
我抹了一把泪水。然后学着父亲的姿式,抬头望了望天空,我发现,蔚蓝的天空里没有一丝云烟。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有侵权行为,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