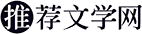一
我家姓王,父亲在湘蜀交界处的中寨里带兵,人都叫他王团总。
不久前,父亲在茶峒河边建了一座碾坊,河水哗啦啦地冲着水车,溅落的水珠映着日光,一闪一闪的,好看极了。水车带动磨盘吱呀呀地转,它们一唱一和,我的心里也咕噜噜地冒着欢快的泡泡。
碾坊为谁而建,为何而建,我自然清楚,那谁又将成为碾坊将来的另一个主人呢?
我希望是船总顺顺家的二老傩送。
父亲也这样想。
二
我是见过傩送的。
十三岁那年的端午节,我跟着父母去茶峒白河边看赛船。河边人群熙熙攘攘,吊脚楼里也是门庭若市,人们虽是名义上来看划船,可聊天谈笑的意思居多,因此大都三三两两聚成一堆,边吃着果子糕点,边交换着这方圆十里八村的奇闻逸事。
河里的四条船却顾不上看客们怎么想,他们只知道自己身上背负着村寨的荣誉,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河弯如弓,船如箭,一声令下,船上的汉子们拼了命得摇起桨,把船划得如离弦的箭一般。
对大人口中的家长里短不感兴趣,我便端了盘点心,找了个僻静处,边吃边看。说来也巧,第一眼望去,我就看见了那个青年,健硕,壮实,高挑,皮肤给太阳晒成麦色,眉眼却是与身型不大相称的清秀。他站在船头,头上包着红巾,上身赤裸,奋力打着鼓点,指挥船的前进。胸膛上泌出的层层汗滴,使他看上去宛若一尊刚涂过油的古铜器,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光。接下来的大半程,我的目光牢牢被他牵引着,纵然河中船只前后交错变换,街上人声纷繁嘈杂,我的眼里变只剩下那块红巾,以及手臂起落间在空中划出的完美弧线。
最终的结果不免令人遗憾,他的船只得了第二。我有些为他不平,看他却是一副开心而无所谓的样子,站他的队员中间,高声说笑着什么,心情便莫名其妙地明朗起来。刚回过神,不远处两个女人的议论声传入耳中:“船总家的两个儿子真是好出息!赛船头两名都让他们抢去了!”
“那第一第二分别是谁?”
“唬。你不知道?第一当然是大老天保,第二嘛,便是傩送二老,人称岳云的。”
“啧啧,看这二老的势头,过不几年必定赶上大老嘞!”
傩送,我暗自记下了这个名字。
下午在河边看捉鸭子,我又见到了他。“傩送。傩送”,心里默默念了他的名字,眼光急切地在人群中穿梭着。
“丫头,看那傩送,多么强劲!”父亲拍拍我的肩。
“谁?哪个是傩送?”我故意向别的方向偏着脑袋,眼睛却不自主地顺着父亲的手指斜过去。
“在那呢,看,他已得了一只鸭子了!你见了他,必定欢喜的!”
“什么鬼话?!”我装作生气的样子撇撇嘴,把头扭向一边,脸颊不知为何突然发起烧来,所幸父亲一直关注着河面,并未在意我的异样。
那天晚间随父母与船总一家告别时,却没能见到傩送,说是玩得尽兴,还在河中没有上来。只有他的兄弟跟了来,那是个与船总顺顺极像的青年,爽朗豁达,憨厚大方,然而看到他时,我的脑海中只浮现出另一张脸。
坐车离开的途中,经过河岸边时,我仿佛听到有人从水中上岸的声响,伴随着几声狗叫和模糊的斥骂,像是个姑娘的声音。
三
再下一年的端午节,我仍是跟了父母到茶峒来,并且由于事务清闲,父亲带我们留下来同船总一家吃了饭,他也在。
席间,我几乎没有怎么动筷,连上了最爱的茶油鸭也没注意,碗筷端在手中,眼光只紧紧随着傩送——他帮忙摆放菜碟利落的样子,大口扒饭却又不似旁人那般粗陋的样子,父兄说话时认真聆听不时赞许点头的样子,被问到意见言语不多却有条有理不卑不亢的样子……
我几乎失了神,一不小心呛着了,拼命地咳,有人在旁边轻轻拍着我的后背,转头去看,刚好碰上母亲含笑的目光,耳朵瞬间烫的要命,握着筷子的手也泌出汗来。
四
许是母亲对父亲说了什么,回到家中不久,父亲同母亲便找我谈话,说我年龄不小了,也该物色个好夫婿了,问我有没有中意的青年。
王家根基在北方,那里黄土连绵,风沙不绝,民风彪悍,生活粗枝大叶,因父亲带兵调动才搬来湘西,再者父亲带兵出身,本就不拘常套小节,因此家风豪放,家人之间向来是有话必讲,从不藏着掖着,与被青山绿水生养着的本地人的含蓄内敛有所不同。
就这样,当父亲问起婚嫁之事时,我虽有几分羞涩,却也毫不迟疑地说出了那个名字。
父母对我的选择甚是满意,顾不得想女向男提亲有什么不妥,便开始为我准备嫁妆,头一件,便是在河边建那座碾坊。
五
碾坊建好了,媒人也派去了,我激动得好几个晚上没睡着觉,等啊等,等啊等,却等来了船总家两个儿子爱上同一个姑娘的消息。
那个姑娘当然不是我。
会不会是媒人没把话说清楚呢,父亲虽建了碾坊,可不是叫他非得一辈子守着不动,他要是想出船,还是可以跟以前一样的,碾坊我一个人也能料理的来……
向来伶牙俐齿言语不饶人的我竟愣愣地说不出话来。
心里一阵失落,原本攥着衣角绞在一起的手瞬间没了力气,浸了不知是紧张还是激动的汗的衣角慢慢平展开来,五脏六腑却皱缩成一团,弄得我有些喘不上气。五月里,指尖竟有些发凉。父母在一旁唉声叹气,感慨这样的事怎么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传消息的人还说,这大佬走的是“车路”,求长辈指婚,那翠翠无父无母,靠爷爷拉扯大,老头子又极疼爱孙女,说要看她的意思,就这么耽搁下了。
“那二老呢?”我下意识想问,却浑身使不上劲。母亲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似的,替我开口问道。
“二老就不一样了,选的是‘马路’,每天夜里跑去姑娘家旁边的高山上给她唱情歌……”
那人后面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只是想象着那朝思暮想的人儿站在高山顶上,月光倾泻在他身上,伴着清亮的歌声,该有多么美。
六
端午临近,父母怕我难受,不让我跟去看船。我却执意要去,为的是见见那位“幸运”的姑娘,据说是渡船老人的孙女,叫翠翠的。
吊脚楼里,我故意跟她坐的很近,细细打量着她,皮肤黑黑的,一条油亮的粗辫挂在脑后,眸子清澈透亮,让人想起山间的黄麂。翠翠瞧人时有些怯怯的,举止倒很大方随性,有股野蛮的孩子气,惹人怜爱。
从我身旁经过时,翠翠迅速地瞧了我一眼,便立刻垂下眼睛,快步走开了。
听人说,大家开始都以为傩送和翠翠是没见过面的,其实两人早在前年端午就打过照面,好像傩送突然从水里窜出来吓着了在岸边等爷爷来接的翠翠,还挨了她好一顿骂。
前年……我默默听着,心好似系上了石头,不停地往下坠。
“也挺好的。”我这样想。什么好?好在哪儿呢?我不知道,就像我也不知道傩送有什么好一样。
七
我没有像戏里演的被心上人抛弃的女孩儿那样要死要活,而是正常吃饭,正常休息,一切都如往常一样。不知是不是家里人想从吃食上补偿我,小半月过去,我反倒比之前圆润了,只是很难对什么事情提起兴致,经常做着什么事突然发起呆来,好半天回不过神。
碾坊刚建好的时候,我最爱往那跑,一待就是小半天。再去的时候,日光灼得人站不住脚,水珠也被烫得四处逃窜,磨盘哎哟哎哟地直叹气,没一会儿我就逃回了家。
父母急急忙忙地为我物色了不少新夫婿,我乖乖跟着他们登门拜访,远远瞧着,那些秀才书生参将公子也都一表人材英姿勃勃,只是我的记性好像变差了许多,等我见过面后回到家,便姓甚名谁连带样貌品格一概不知了。
就连傩送,我也很难十分清晰地刻画出他的模样,脑海里只剩下那年端午,阳光明媚,人头攒动,那一个包着红巾击鼓赛船的少年。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开始发急,“碾坊建好了,总不能没有当家人!”
我不答话,低头看着脚尖,忽然想起之前有双很好看的绣花鞋,原是预备嫁人的时候穿的,现在用不着了总不能浪费,便在心里细细盘算着周围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女孩儿,打算送给她们。
母亲柔声细语地劝着父亲,说再给我些时日。
两道担忧地目光落在我身上,我毫不在意地夹起一块茶油鸭,面无表情地就着米饭咽下去。嗯,真香。
父亲很长地叹了口气,大踏步地离开了。
八
不久后的某一天,父母留我一人在家,外出吊唁不知道什么人。我没多问,几天后才知道船总家大老溺水而死,二老悲痛远行的消息。
不久,翠翠的爷爷去世。她一定伤心极了,我想要为她做些什么,却最终什么也没有做。
人们都在说可惜了翠翠和傩送这对有情人,又说翠翠独自一人守着渡船,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那我呢?
我该怎么办?
还要等下去吗?
等到什么时候呢?
也许再也不等了,也许永远等下去。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有侵权行为,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