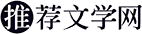《夜鹰》Nighthawks 1942年
11月后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下午,进入上海博物馆仍需要排着长队。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 1882-1967年)76年前创作的《夜鹰》(Nighthawks),就挂在这家博物馆二楼的展厅里。
一,寂静的鱼缸和人类标本二楼的走廊上,它被喷绘成巨大的广告牌,作为这场“走向现代主义:美国艺术八十载(1865-1945)”展览的招贴画,占据了半面墙壁。随人流鱼贯前行,看了一圈温斯洛·霍默、惠斯勒、卡萨特和欧姬芙们后,终于见到《夜鹰》。画中餐厅顶部投下的那道光线纯正、耀眼,像一把锋利的刀刺破午夜寂静的空气,你几乎能听到被巨幅玻璃封闭的餐厅里,发出某种细微的金属撞击声。
主办方为它搭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在前方放置了一张长凳。但如果你想要坐在这张凳子上,安静地与这幅画对视一会儿,则几乎不可能,因为总会不断有人过来对着它拍照。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在这个最为拥挤、嘈杂和扭曲的城市里,看到70多年前纽约午夜街头的这家冷清餐厅,这种感觉多少有些奇怪和反讽。
显然,在这整个展厅里,《夜鹰》是所有画作中辨识度最高的一幅。拥挤到它面前的人们,都为从它身上获得的某种熟悉、固化的、可以确认的美学见解而振奋。
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夜鹰》摄影:船长
《宾夕法尼亚的清晨》 1942年
在展厅的另一侧,是霍普同年完成的另一幅《宾夕法尼亚的清晨》(Dawn in Pennsylvania 1942年),就没遭遇到如此的围观,那场面正像画作中的火车站台,在宾夕法尼亚黎明的钢蓝色天空映衬下,显得分外落寞、寂静和空旷。
霍普的妻子约瑟芬·霍普也是一位画家,在她的日记里会对霍普的创作过程以及技术细节做详尽记录。按照约瑟芬的记载,这幅画作之所以取名为《夜鹰》,源自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对中间这位戴礼帽的男子取的绰号,他们将这位有着一个喙状鼻子的男士称做“夜鹰”,她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一形象的诞生过程——男子夜鹰(喙)着深色西装,钢灰色帽子,黑色带子,蓝色衬衫(干净)拿着香烟(Man night hawk (beak) in dark suit, steel grey hat, black band, blue shirt (clean) holding cigarette)...
1942年1月,约瑟芬在给霍普妹妹的信中再次提到了这幅画的名字,“夜鹰将是为这幅画一个合适的名字,”她写道。她还描述了画中人物的模特也来自她和霍普,她扮演的那个女孩的形象,而霍普自己对着镜子摆出了两位头戴礼帽男士的造型。
据约瑟芬的描述,《夜鹰》具体完成时间是1942年1月21日,霍普用了一个半月完成了这幅画作。
如此推算,这幅画作应该是在1941年年底开始动笔。而那正是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间节点——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瓦胡岛上的飞机场,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此时的历史,已经变身为一头狂暴咆哮的庞大怪兽,但霍普并没有为我们描绘这头怪兽凶悍的面貌,也没有描绘它巨大的力量和残忍地动作,霍普仅仅从这头怪兽庞大无边的身躯上抽取了一滴血。当他把这滴血描绘在画布上时,我们在瞬间就看清了那时纽约的孤寂、焦虑、冷漠和百无聊赖。
整幅画作中的情节、人物、构图、色彩都显得极其冷静,透着巨幅的玻璃,我们所看到了这几位顾客和侍者,他们之间原本可能毫无关系,但在此刻同处于这一空间,像是被放置,或者被囚禁在一个巨大空旷的鱼缸里。而画家的视觉和观众的视觉一样,我们就像宇宙中的另一群生物,正注视着这几位人类标本。
《夜鹰》细部1
《夜鹰》细部2
有人认为霍普的灵感可能来自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杀手》(The Killers),因为霍普很欣赏这本小说,同时画面里的情节也和小说内容一开始的场景吻合,因此有人说《夜鹰》描绘一个故事的开始部分。至于餐厅是否存在,霍普本人曾说,餐厅的原型来自由格林威治大道边,两条相交街口的一家餐厅,他在画中对场景进行了简化,并且扩大了餐厅的面积。也有人按图索骥去格林威治村寻找这家餐厅,但一无所获。
这些细节也许并不那么重要,对于一些重要的作品,包括画家本人对着媒体或者公众不断解释、然后不断被引用、重复的那些细节和注解,并非其关键所在。画家本人也往往难以复原当初创作时的触发自己的隐蔽动机。更也许,在创作时,他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
比如人们注意到霍普并没有为进入这个玻璃餐厅留下一道宽阔气派的大门,侍者身边那道小门看上去像是通向厨房或者杂物间——在张靓颖拍摄的MTV中就从这道小门进出的——这也许想表现“囚禁与限制的主题。”但他霍普仅承认:“也许,我的确是无意识地在描绘一个大城市的孤独。”
2016年张靓颖mtv画面截屏 来源:网络
2016年张靓颖mtv画面截屏 来源:网络
当然霍普并没有像基里科、玛格丽特或者达利那样刻意地追求超现实主义,但是他的确表示过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知识、潜意识理论有浓厚兴趣,他也曾写道:“每一门艺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潜意识的表现,我认为最重要的品质似乎都是无意识地放在那里的,而有意识的智力却没有多大的重要性。”
由此,我们便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把另一侧的街道与建筑物的窗户中,处理成和基里科 (C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一样杳无人烟的样子。(有关形而上学画派、超现实主义先驱画家籍里科的介绍,可参阅本号文章《从无人超市到基里科的无人广场》)
我不能妄言霍普是否受到基里科的影响,或者作为同时代的画家采取了一种殊途同归的创作理论,但《夜鹰》确实使我联想到基里科说过的那句话:
“一个人必须把世界上的一切描绘成一个谜,并居住在这世界里,如同居住在一个巨大陌生的博物馆中一样。”
基里科:《一条街上的忧郁和神秘》
二,风格的形成与异化的现代生活与超现实主义者们不同的是,霍普并不刻意强调和描绘创作者自身的梦境、潜意识、谵妄等意象,他只是一位冷静的现实旁观者,但他这种疏离的观察者态度,确实为我们描绘了正在做梦的城市与城市中做着各种梦的人。
爱德华·霍普师承垃圾桶画派(Ashcan School)的精神领袖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i),他的创作生涯纵贯20世纪前半期的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从进步时代到咆哮的20年代,然后是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直到二战后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等等社会、哲学、文学思潮。
霍普的画作主题,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其笔下的美国城市,并不像几十年前亨利或者贝洛斯等等垃圾桶画派前辈们所描绘的那种脏、乱、差的感觉,也不同于19、20世纪之交时美国印象派画家们笔下的城市,那时的画家们敏锐地抓住了都市生活中最残酷的时刻,或者着力于描绘都市中正在发生的奇妙景观,还没有形成对城市——这一人造工业景观的系统反省、批判中。
然而在霍普的画作中,无论是工厂、加油站,还是城市街道的某个角落,其建筑与空间都显得干净,整洁,但这种整洁中都透露出一种深入骨髓的冷清,他所制造的忧郁氛围、落寞情调就像工厂中制造出来的水泥模型一样精确,那些光线与阴影锋利得如刀一样,切割着时间,让画面中的人,在现代城市中显得彼此隔阂,因而孤独并无奈。
Automat 1927年
Early Sunday Morning 1930年
Office in a Small City 1953年
Manhattan Bridge Loop 1948年
爱德华·霍普出生于纽约州的奈亚镇(Nyack),年少时不太合群,喜欢独处,养成了从喧嚣中洞察细节的细致观察力。长大后,他在纽约市学习商业艺术与绘画。他于1906年到1910年间,曾三次到欧洲旅行,可能是因为从小性格孤僻,在欧洲期间没有太多社交活动,也没有融入当地的艺术圈子。
欧洲的游历给了霍普一些启发,他明白自己需要表达的是真正的美国式艺术。虽然他对当时欧洲先锋绘画有过研究,但他并没有皈依当时流行的野兽派那些绚丽的色彩,或者像立体主义那样用柱体、球体去构建画面空间,他忠实于自己对纽约这类城市的真实感受。他认为,自己除了受到有色盲病症的法国雕刻家查尔斯·梅里扬(Charles MéRoun)的影响以外,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影响。
从欧洲回到美国后,他在纽约市租了一间工作室,极为勉强地位一些杂志画插画来养活自己。但他还没有寻觅到属于自己的风格。
而当婚姻到来后,霍普终于有了自己的风格突破。
1923年暑期,已经是41岁的霍普在马萨诸塞州的写生之旅中,遇到了同样是罗伯特·亨利学生的约瑟芬·尼维森(Joseph Nivison),约瑟芬与他在各个方面都截然不同,她个子矮小、性格开朗、善于交际,与腼腆内向的霍普完全不一样。一年后,这两位性格互补的中年人终于结婚了。
也就在结婚这年,霍普买了一辆二手道奇车,从纽约一直开到新墨西哥。还是在这一年,霍普完成了自己标志性的作品——《铁道旁的房屋》(House by the Railroad),由此霍普式的风格开始确立。
《铁道旁的房屋》(House by the Railroad)1925年
这个矗立在铁道一旁的陈旧房屋,曾经是庄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豪宅,但现在在阳光的照耀下,却显得出奇的寂寞,成为一处被铁路所连接的、远方城市的现代文明所抛弃的陈旧景观——以《铁道旁的房屋》开始,标志着霍普式的独特美学逐渐完成。
典型的霍普式美学风格包括以下一些特征:选择生活中常见场景的一个角落,比如加油站、电影院、咖啡馆、火车车厢等等;采用锐利的线调和大幅的块面;诡异极不自然的人造灯光。霍普是光线与构图的大师,他善于利用这二者来营造一种隐秘,但又充满丰富感情的情节。他经常用水平的道路或者铁轨、站台,建构画面的空间,以此强调观众和画面的距离。
后期霍普作品的创作主题,集中在展现这类美国社会的真实图景,用个人独特的视角重新思考现代美国的艺术内涵:现代生活的异化,在冰冷的工业设施或者城市建筑间,生活中的美国富裕而迷茫的中产阶级,他们孤独、彼此疏离、隔绝,这些人被困在霍普所创造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空间中。他们,既没有回忆,也没有目标——就像今天的我们。
正在上博举办的走向现代主义画展 摄影:船长
1967年,爱德华在纽约市华盛顿广场区的画室去世,他的妻子乔瑟芬·尼维森在他去世十个月後,也离开了人间。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有侵权行为,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