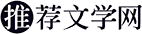郭姣萌勾着脑袋,仿佛睡着了,双肩时不时动一下,头发散开,盖住了耳朵。周围十分安静,只有火堆上柴燃烧偶尔发出的一声炸响和柴里水气过重冒一些吐水珠滋滋的细声。突然,有一块烧断的柴哗垮了下来。
火花飞溅。在他们面前仿佛是化成了一只一只灰白色小蝴蝶。
王琦听到从遥远的地方(大概是从江上)传来细丝如缕的情歌,他屏息敛气,仍听不太明白。“红尘中到处都是无辜的爱,男女老少连夜在自己的内心遇难。被诗歌埋没了一生的人,骑着梦中那只忧伤的豹子,冬天去人间大爱中取暖,夏天去佛法中乘凉。丧钟响了,人人都故意迟到。”
还以为是央宗在唱。
但知道并不是。
“你等等!”他叫喊道,“你奶奶她恐怕读过汉人的书。”
央宗说,我奶奶本就是汉人。
“我知道的,你白天对我说过。”
“那时,天已经黑了。”
是啊天黑尽了。满苍穹,水洗过一样分布星斗,干净而神秘。
他们抬头望去。
“还会有一艘月芽小船,平安驶过弯弯的天幕。船上的人喝醉了。”央宗说,“我奶奶九十多岁了,但她的记性特别好,她说,小时候她唱过的歌一辈子她都忘不掉。她其实很少对哪个谈起她自个儿小时候的那些事,远得比天上的星星都远,她究竟读没读过书我确实不清楚,她不说当然没人晓得,估计我阿爸阿妈也不会知道,从来都没人说起过。”
王琦问:“见过你爷爷吗?”
她说早都去了天国,连她都从未见过。
“奶奶何止是读过书啊!”王琦连声叹息。
央宗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奶奶的文化程度多半还不低。”
王琦又问:“奶奶是哪里的人,知道不?”
她立马说不晓得,反正只知道她是汉人。他说,说不定她还出身名门,是个大家闺秀。
“你会算命?”
央宗笑道。王琦说,我不会算命,只是推测。
“不晓得!”央宗摇头。
王琦想,央宗的奶奶就算不是出身名门,也肯定是进过学堂的女性,八九十年前,会是什么样的人家才让女孩子去读书呢。也许,她正在去上学的路上,便让人背了娃子。他猜想当年奶奶说不定只有八九岁,十多岁,是读了书的新女性。那故事好凄惨好悲壮的。也许是她一路上正走着,正在背情诗。她穿着学生裙,或者是走在朝露里,或走在一片落日余晖中,她跨过了一座小小石拱桥,独自走在那条冷清的泥巴路上,小路弯弯曲曲的,她走在拉拉蔓粉红色艳丽的花丛中,蒲公英的白色小伞正在她的四周围升飞。一路上,她仍然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也许她年龄还大点,懵懵懂懂恋爱了,傻呵呵的,正想着她心中所爱的男同学。她曾经有过一段惊天动地的爱情吧,火烙过一样,至死都忘不掉。这时候,她突然被袭击。
有人冲来把她塞在了一个麻布口袋里,她看不见阳光了。别人把她扛着跑。从此她便远离了故乡。再后来她逐渐老了,每天只能够坐在火塘边上,靠讲故事来打发剩下光阴。
他大声说:“我肯定要拜访你奶奶。”
“扎西怎么还不回来!这家伙办事就喜欢磨蹭。”央宗话题一转,对王琦说,“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吧,反正也是打发时间。光干坐烤火,怕我们大家会感到无聊。”
“我姐,你别尽说一些吓唬人的故事!”
晋林抬起头来。
王琦感觉到自己手和脚又能够活动自如了。
他站起来,甩几下手臂,原地踏步,溅起来了许多柴灰。郭姣萌真的是睡着了,双肩轻轻颤动。在她身后站了几分钟,听到她细细的扑鼾声音。这样的夜晚,身处这样一个遗世独立的伐木场,扑朔迷离。他用手乱舞动了一下,想赶走那些灰土。柴灰有一股咸味儿,干燥,但不呛鼻子。他围着大火堆慢慢地走几圈,本来是想小跑的。央宗劝他别着急。王琦也觉得自己穿着短裤,上身又穿件夹克,绕着火堆这样小跑肯定特别可笑。他假装一幅若无其事的样子,再走上几圈,让手脚活动开。身体不是正常的暖和,而是一边滚烫而另外一边差不多冰凉。但是不再僵了,不像先前,仿佛从皮肤一直到心脏都冻僵了。甚至,不属于自己所有。这时候血液缓过气来了,大概是又重新在他体内奔流。他想找个地方解小手,便绕到那一大堆木材背后去。吹来一小股风,冰冷的。他心想,幸亏是没有下雨。仍然可以看到满天星星,虽然月芽迟迟不肯出来。远离了火堆,马上觉得那边可真的是冷。气温降低到他难以想象,这可是夏天。他直接怀疑,嘴上嘟哝。王琦浑身肌肉纠缩,打了个冷噤,哦哟,怎么彻骨冷,千万别搞感冒才好。好像的确是有点发烧了。他想。在这个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伐木场上病倒的话情况真的是很糟糕。他又快速回到了火边。
他听见不远处有响动,是鞋子踢着石子或踩断了一截干柴的声音。王琦抬起眼睛来,眨巴眨巴眼睛,瞧见了一个模糊的人影,走得有些东倒西歪的。很快他也就走近了,看清楚是扎西回来了。隔着一大堆木材,风带着他的气息,直逼过来,他闻到了一股酒味。
扎西浓浓的体味呢?
他只替王琦借到一件军大衣。
他穿在身上带回来的。大家这时候都闻到了他身上的那一股酒味。和一股风朝他们扑来。刚见面,扎西怒气冲冲地朝央宗叽哩呱啦大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他把军大衣脱下来披在王琦身上。等他坐在一个树桩子上,嘴里仍然还在报怨。“扎西说什么?”王琦问央宗。
“他说司机开车跑了。”央宗说,脸部没有什么特别表情。
“啊,那可怎么办?"王琦又问了一句。
“什么怎么办。”央宗说。
他们低头直勾勾瞧着火焰。
“收了费的,不讲信用。”
王琦也有点气愤。
“他有什么信用好讲。”央宗笑道。
“那个秃头,狗杂种!在前面提前把那家伙抢了就啥事也没有了,我看他跑。”晋林显得十分沮丧,“他本来没有一点逃走的机会。”他说完这句话瞟了王琦两眼。
郭姣萌醒了,抬起头,把头发撸到脑后,转头望着王琦,露出惊惶。许多年后,郭姣萌还回忆起当初的情形说她顿时被吓懵了,脑筋短路,一片空白。那次的危险经历成了她炫耀的资本,一生的骄傲。大概她都没听明白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别怕。”她用手掌拍拍郭姣萌的膝盖。
“晋林你别胡说行不行!”
央宗冲她弟弟大声叫喊。
“有啥子好隐瞒的,”晋林说,“本来就是。我有啥子说啥子,他不仁我就不义。”
央宗说:“你们想吓着客人!”
“王琦又不是没看出来,他人本来那么聪明。”
她大呼小叫看出了什么。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有侵权行为,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