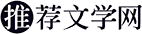在12月底的日子里,西方 人开始欢度他们的圣诞节,而 东方人的节日则是冬至。 当然,严格地说,冬至算 不得节日,即便是,也不是人 间的,而是另一个世界的,也 就是中国人所谓鬼魂的节日。 但相对于圣诞节,西方人也许 更喜欢圣诞夜,并冠之以种种 美丽的称谓,比如平安夜。冬 至也是,不过冬至前夜是比较 晦气的,尤其是对于偏好于传 统的老人们而言。
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在北半球,冬至是夜晚最长、白昼 最短的一天,如果把一年比作 一天,冬至就等于是子夜。所 以,冬至的前夜是名副其实的 漫漫长夜,天黑得特别早,也 特别冷,太阳总是若有若无地 挣扎着要提前下班,仿佛患了 黑暗恐惧症一般急急地躲到地 平线以下去。天空已是一片 漆黑,几乎连月亮都找不到 了,我站在窗前,望着远方的 乌黑的天空,心中忽然有了种 奇怪的感觉。
现在 已经快深夜,难道真有 这么重要的事?会不会开我玩 笑?不过林树不是这种人,他 这种比较严肃的人是不太会跟 别人开玩笑的,也许真的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 我在房间里徘徊了一圈, 然后看了看漆黑的窗外,最后 还是决定去一次。 出了门,发现地上有好几 圈黄色的灰烬,不知是谁家烧 过的锡箔,我特意绕道而行。
走到马路上,才发觉天气要比 我想象的还要冷,风不知从什 么地方窜出来在半空中打着唿 哨。商店都关门了,开着的便 利店也是了无生气的样子,人 行道上几乎没有一个行人,就 连马路上的汽车也非常少,我 等出租车等了很久,清楚地数着在空旷的黑夜里回响的自己 的脚步声。 终于叫到了一辆出租车。 驾驶员30多岁,挺健谈 的:“先生,今天晚上你还出 去啊。 ” “有点急事。 ” “明天是冬至啊。” “呵呵,我不信这个 的。 ” “我也不信,可是今晚这 日子最好还是待在家里。今天 做完了你这笔生意,我马上就 回家,每年的今晚我都是提前回家的。” “为什么?” “鬼也要叫出租车的嘛。 因为今晚和明天是鬼放假的日 子。没吓着你吧,呵呵,开玩 笑的,别害怕。” 车上了高架,我看着车窗 外我们的城市,桑塔纳飞驰, 两边的高层建筑向后奔跑,我 如同在树林中穿行。迷蒙的黑 夜里,从无数窗户中闪烁出的 灯光都有些晦暗,就连霓虹灯 也仿佛卸了妆的女人一样苍 白。
不知怎么,我心神不安。车子已经开出了内环线。 林树的家在徐汇区南面靠近莘 庄的一个偏僻的居民区,七 楼,一百多个平方,离地铁也 很远,上个月林树说他的父母 到澳大利亚探亲去了,要在那 儿迎接新世纪,所以现在他一 个人住。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 子,要有点心理素质的。 我看了看四周,现在车子 开在一条小马路上,虽然林树 的家我常去,但从没来过这条 马路,黑夜里看不清两边的路 牌,只能看到远处黑黑的房 子,要么就是大片大片的荒 地。车子打着大光灯,照亮了正前方,光亮的柏油路面发出 刺目的反光。而四周是一片黑 暗,如同冬夜里的大海,我们 的车就似大海里一叶点着灯的 扁舟,行驶在迷途的航线上。
我索性闭上了眼睛,迷迷 糊糊地任车子载着我在黑夜里 漫游。在半梦半醒中,车子忽 然停了下来,我睁开眼睛,看 到车外一栋栋黑黑的居民楼, 的确到了。我下了车,司机只 收了我个整数,零头不要了。 然后他迅速掉转车头开走了。 我懵头懵脑地向前走着, 不住地哆嗦,小区的弄堂里不我看了看时间,快12点 了,把这个时间让给他们的两 人世界吧,于是我向陆白道别 了,其他人也纷纷识趣地走 了,只留下他们两个在黄浦江 堤边卿卿我我。
我望了望四周,还有许多 一对一对地在寒风中依偎着。 我竖着领子,沿着黄浦江走了 几十步,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女 人的尖叫声。那又高又尖的声 音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划过平安 夜的空气,我脆弱的心脏仿佛 有瞬间被它撕裂的感觉。我捂 住胸口,自己的心简直要从嗓 子眼里跳出来了,这时我听到许多人奔跑的声音,而女人尖 厉骇人的叫声还在继续。我回 过头去,看到发出尖叫的正是 陆白的女朋友黄韵。我愣了一 下,随即冲了过去,挤开人 群,看到人们都在往黄浦江里 张望。我也往江里看了看,黑 漆漆的江面卷起一阵寒风, 个人影在江水里扑腾挣扎着, 升上一些微弱的热气,然后渐 渐地消失在冰凉刺骨的滚滚波 涛中。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有侵权行为,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